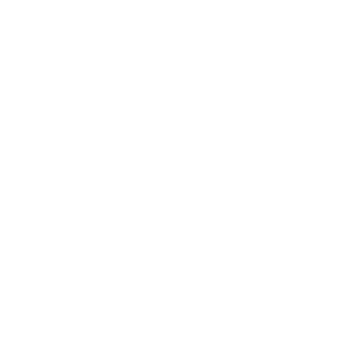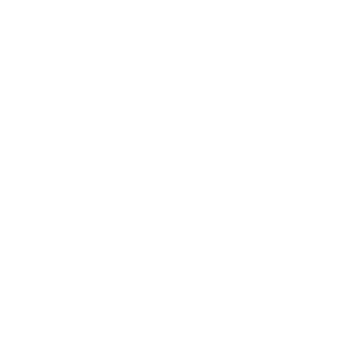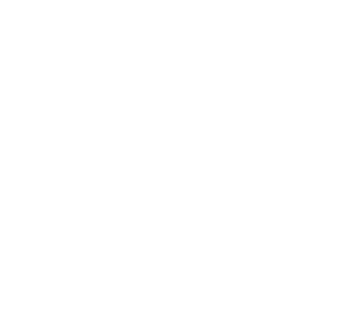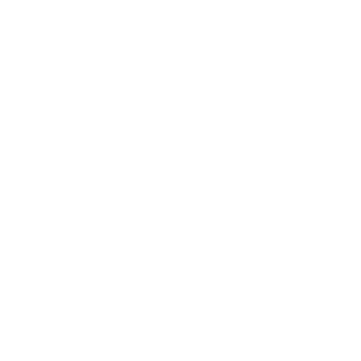精神的再現──岑龍繪畫中的永恆追求
藝評|陳貺怡
陳貺怡
10/6/2023
岑龍的繪畫在五光十色、紛紛擾擾的當代藝術中,因為特別的節制與樸素,反而顯得格外突出。這種樸素的感覺,首先來自於單純的構圖與節制的用色:事實上,岑龍早期雖曾到處寫生,畫過河南、湖北、西藏、新疆等地的景物,也嘗試過不少複雜的構圖,但在2010年畫了以但丁《神曲》中的〈淨界〉為題的巨幅三聯屏之後,彷彿受到了啟發,從此進入另一個全新的階段。此作置中的是一棵沐浴在月光下的盤根錯節的古木,左屏是一位在石頭路上俯身點燃油燈的僧侶,右屏則是一位在暗夜的風帆中拉起燈籠的水手。半裸的男性人物肌肉精實,且手腳超乎尋常比例的巨大,呈現出勞動者的莊嚴姿態,同時也為暗夜孤獨崎嶇的旅程帶來光明與希望。
從此,岑龍醉心於如此的創作方式,他幾乎只使用黑白灰作為主調,再以赭黃、棕褐色的暖,與藏青色的寒加以烘托,並盡量壓低彩度以維持中性色調。他的素描技巧與造形掌握力都很高超,人物比例略帶誇張,在略顯戲劇性的光暗處理下體感渾圓厚實。而他以人物為主的構圖也愈趨精簡,經常只針對個別人物進行彷彿肖像畫般的描寫,或者繪製至多二、三人或有動物的群像,但背景的處理方式經常只以色帶粗略的標示出天地際分,甚至只以充滿搶眼筆觸的單色塗滿,以至於失去明確的時間與空間,表達出了一種永恆感(timeless)。至於畫中的人物,經常穿著樸實,甚至裸露著上身,僅像古希臘的雕像般以衫裙遮蔽下身。而裸體並非不具意義,它消弭了象徵人物社會身分的衣物,回歸其最真實與原初的狀態。裸體在古典主義中更意味著理想化的身體,是英雄或神祇精神自由之象徵。雖然這些人物的身分因著他們的動作與持有的物件,看起來仍像是他一直以來關注的農夫、牧人、漁夫、樵夫、婦人與孩童,身邊伴隨著協助勞作的動物,並無不流露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質樸生活與辛勤勞動之價值。但是在新的系列中,岑龍顯然拋開了對特定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的描寫,畫中的人物彷彿失去了特定意義與語境的符號。再細品,畫與畫之間似乎存在著某些巧妙的關聯:例如〈蒼穹星光〉中左手持槳、右手持燈,仰望星空的男人;或是〈起風的日子〉中貌似奮力拉起風帆的二人,是否與〈淨界〉中的水手有關聯呢?而〈福音〉中扶著十字型的杖,閉眼祈禱的少年,與身邊飛過的白鴿;或〈迷途的羔羊〉中向耶穌一樣尋找並帶回小羊羔的婦人,是否都是〈淨界〉中僧侶的對應?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這些不斷重複出現的「母題」(motif):船隻、風帆、槳、燈、星星、羊、白鴿、參天古木等等都是一些乘載著訊息的符號?或像是無固定符旨的符徵,自然而然地帶出意涵的豐富性與詮釋的開放性?
更值得一提的是岑龍採取的「聯屏」形式,雖然在展示時並非必然,但明顯可見許多畫作在畫幅大小形狀上的相似,以及主題之間的彼此串聯,似乎足以在概念上構成聯屏。聯屏來自於祭壇畫,不僅具有宗教性,而且根據德勒茲(Gilles Deleuze)所言,聯屏彷彿音樂中的樂章般分配節奏,或基本的節奏形式。他指出由於畫中貫穿著極多的運動,所以聯屏的法則是一種「運動的運動,或者是一種複雜的力量狀態」。以聯屏的方式構成的畫作,無疑的比諸自成一格的單幅繪畫多了許多節奏、運動與力量。而這些貫穿於畫與畫之間的符號鎖鏈與形式特徵,共構了繁複的象徵系統,飽含潛力與不透明性,力邀觀眾們解鎖畫家內在世界的奧秘。這種隱喻性的繪畫方式,顯然將岑龍帶進了象徵主義;而單純的構圖、巨碑式的尺幅、內斂的色彩,以及充滿力量的粗獷筆觸,則使畫作散發出一種沉靜的吸引力,藝術家似乎試圖在今世的撩亂與喧囂中,營造一個心靈安歇之所。
岑龍從小浸淫於西方古典繪畫原作,觀察上述創作特色,可以斷言他受到西方古典美學思想與大師經典傑作的影響很深。自上古時期始,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即認為繪畫的本質是「模仿」(la Mimèsis),但模仿的對象必須是人類行動中最高貴者,以滿足藝術的教化功能。而岑龍壓抑色彩,強調disegno(義大利文「繪圖」之義)的繪畫方式,在十六世紀時即為瓦沙里(GiorgioVasari, 1511-1574)所極力推崇。後者認為disegno除了「描繪」之外,更意味著「構思」、「意圖」與「發明」(invention),並非只是對象物外形輪廓的再現,更是「精神的再現」(représentation mentale)。而古典主義的大師們,也咸認為對於魅惑感官之色彩的壓抑,更能達到再現精神的目的。岑龍在如此的美學基礎之上,創作出充滿哲理與精神內涵、足以與大師的傑作對話的藝術作品。他的〈迷途的羔羊〉就如同林布蘭特(Rembrandt vanRijn, 1606-1669)的〈浪子〉一樣扣人心弦;他的〈阿米子與花花〉就像米勒(Jean-François Millet, 1856-58)的〈拾穗〉一樣充滿勞動者的尊嚴;他的〈我們播種希望〉、〈歸途〉或〈家人〉就像米勒的〈賦歸或黃昏之星〉(TheReturn from the Fields or The Evening Star, 1873)一樣洋溢著家人之間樸實無華的情感。但岑龍顯然是一位高明的經典致敬者,他並非一昧地模仿前人,而是將歷世歷代觸動人心的文藝經典當作精神糧食,反覆咀嚼吞嚥,再吸收為創作養分,以至於畫中那些尋常的人物,個個擁有英雄般的氣魄與高潔的靈魂。
繼承自西方的美學,與得自於經典傑作的養分,卻使岑龍的畫作在今日顯得不合時宜,看起來既不新潮也不前衛,既引不起當前的話題也未能迎合多變的當代藝術市場。但我認為岑龍的作品在當代繪畫中的意義,應當可與著名的挪威畫家納德盧姆(Odd Nerdrum, 1944- )相提並論。後者也同樣對現代藝術「感到疲勞與厭惡」,卻對林布蘭特的作品感動不已;同樣反對文化官僚主義,同樣忘我於一己的內在世界,同樣透過對藝術史經典大師的致敬來批判當今社會;更同樣圍繞著但丁的「靈薄獄」 (limbo,即岑龍的「淨界」)來建立象徵主義式的創作脈絡;並同樣為了景仰神創造的崇高而選擇長居不毛之地。靈薄獄是靈魂將去之處,眾生在此等候救贖,而繪畫顯然也成了藝術家的救贖。我們可以稱這種面對繪畫的態度為「反現代」,因為當1863年波特萊爾提出「現代性」時,明確的定義現代性是「短暫、稍縱即逝、偶然」,但他也不諱言這只是藝術的一半,而另一半則是「永恆不變」。很明顯的,岑龍選擇了另一半,也就是不論外在世界如何日新月異都不會改變的那一半,彷如他在真誠的自剖中寫下的:「我頓悟了;藝術作品內在的美感才是藝術家永恆的追求」。而如此的追求既不受限於時空,更可說是無比的當代,因為對「現代」的批判與反思,正是當代藝術的本質之一。





來源|Artouch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