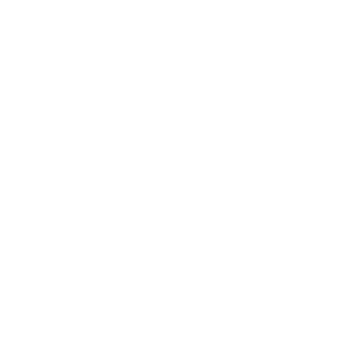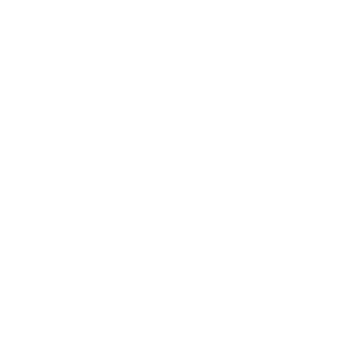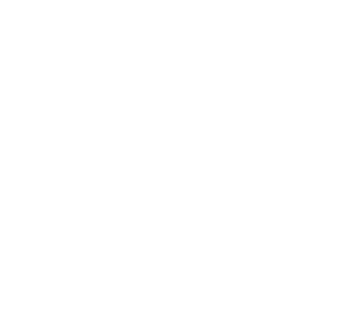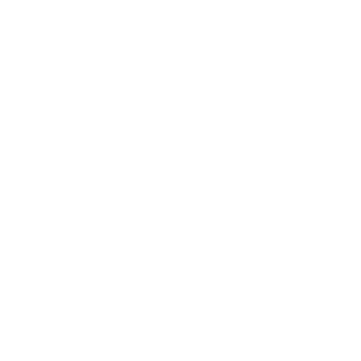2016 - 漆黑的夜晚
1/1/2016
很早我就非常熟悉一首俄羅斯歌曲〈漆黑的夜晚〉,每當我感到寂寞的時候,就會想到它。
十幾歲時,父母因受到文革政治迫害雙雙被關押,父親因此丟了性命。他們的工資被凍結,我的弟弟剛剛上小學。經高中同學介紹,我到鐵路機務段做學徒,接替那些外出造反的工人。那裡包三餐飯,一天五角錢的收入夠弟弟吃六碗麵了。當時一切都十分混亂,人們全都狂熱到了極點,幾乎沒人上班,工作崗位嚴重缺員,機車大量滯留,鐵路運輸幾乎癱瘓。我雖然剛剛夠那把鏟煤的鐵鍬柄高,但是經過短時間訓練,就上了火車擔任司爐學徒工,其實也就是完全替代了正式工。
我記得那是一台車號是PL002,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的PL9 型小火車。我愛死了這個被工人們戲稱為「破落九」的老舊大玩具,天天都要把它上面的黃銅件擦得晶亮。每跑一趟車,我就要用鐵鏟將煤水車上的12噸煤塊一鏟鏟送進爐膛,用右手翻動鍬把和旋動手腕,用左手控制鐵鍬送出的方向等一系列專門動作,將煤塊煤粉撒入爐內四個角落以及爐膛中央,使爐床鋪成吻合鍋爐的弧狀,均勻燃燒,燒足十二個氣壓的蒸氣來供火車正常開動。我學會了瞭望前方的翼板信號燈:豎大姆指表示正線通過,側大姆指表示斜線通過,還要與司機、副司機同時喊話,表示三人的觀察結論一致。我也得常常打開水泵開關幫鍋爐加水,免得鍋爐被燒乾引起爆炸,這些等等都是我終生難忘的經歷。
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夜間行車;那時候沒有太多的城市開發,中國大部分地區是鄉村農田,因為電力不普及,很多地方還是依靠煤油燈照明。入夜,四周一片黑暗,只有火車開動的轟隆聲響,車頭的探照燈直楞楞地照射著前方路軌,司機和副司機在講著我聽不太懂的黃色笑話和家常。那是個漫長又特別無聊的時光。我經常站在連結火車機車與煤水車之間,抓住護欄的鐵鏈及銅拉手,把頭探出去,任強烈的疾風刮著被爐膛灼痛的臉龐,睜大雙眼向原野張望,一遍又一遍在心裡哼唱〈漆黑的夜晚〉(俄文是:Тёмная ночь)。 忽然遠方出現一處微弱的燈光,由遠及近,忽閃著,我的心跳也會隨著燈光的變幻加快,因為一盞小小的燈就是一個家庭。在我的想像中,「家」一定是很溫馨的,也許一家人圍在燈下聊天,還會有隻小狗小貓什麼的伏在一旁⋯⋯
這段漫長的日子裡,燈光成了我心中的希冀和安慰,每當一處燈光快速地被甩在後面,但又可以期待著另一處燈光的出現,每一道亮光如同一次新的希望。這種情形使我無視生活的苦難和憂傷,更為幸運的是:我的內心裡擁有著一處僅屬於自己的想像世界;我回憶著文革前,少年時期有幸拜讀過的果戈里、契訶夫、托爾斯泰、海明威、聶魯達、雨果、巴爾扎克、斯湯達、普希金、萊蒙托夫、拜倫、朗費羅、雪萊、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中的詩句和篇章,尤其是俄羅斯現代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關於安徒生的故事〈夜行的驛車〉,聆聽過的蕭邦、李斯特、莫札特、貝多芬等人的旋律和樂句,欣賞到的列賓、蘇里科夫、列維坦、弗盧拜爾等畫家的畫作⋯⋯
有這些珍貴的精神食糧滋潤著我,有這些不朽的大師伴護著我,在這一個個漆黑無眠的夜晚,我暫時忘掉了不久前被抄家之後,一家人被限制在狹窄擁擠的小房間裡那面面相覷的恐懼絕望和無助,也忘掉了不久前一個悶熱的夏夜,光著腳的父親被一群帶著猩紅血色袖章的紅衛兵用棍棒押走,我追上去被推倒在石子路上,從此父親永遠不能回家相聚,哪怕以前和後來人們稱他為「文化大師」,更忘掉了不久前,不會做飯的我和弟弟從學院食堂買飯,送給被關押的做歷史教授的母親吃,看守她的工人宣傳隊頭目打開鍋蓋檢查時,不屑地冷笑著說:「她還有資格吃這麼好的飯!」當時我用僅有的幾角錢買的是素炒捲心菜,一丁點油也沒有⋯⋯
我真正體會到藝術的力量真大,大過了這漆黑寂寞空曠無邊的夜晚。我思忖著:這些散佈在大地上的燈火似是人間的溫情,而那些偉大的藝術創造者們有如天上的繁星,他們聚合一起在我們因暗夜而變得陰鬱的心中點燃起一束希望的光,正像火車頭上的探照燈發出如利劍般的強光,刺破漆黑的夜空,照明著通向終極目標的前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