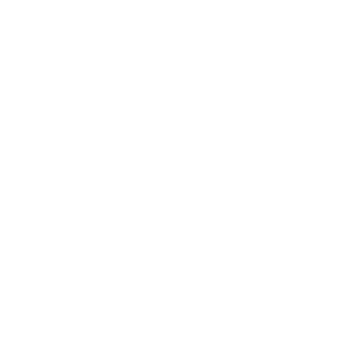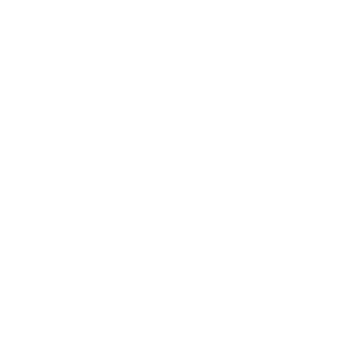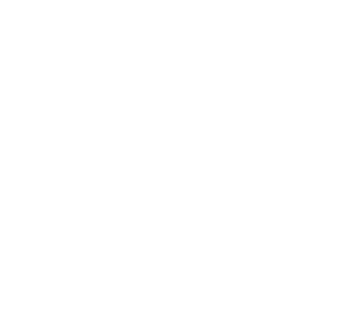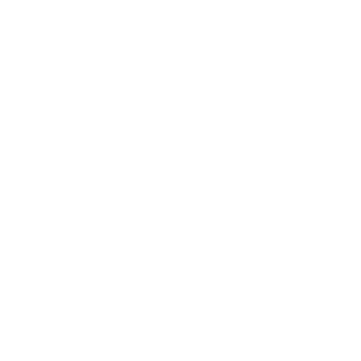簡秀枝 - 藝術家岑龍在繪畫中找到愛與希望
NEWS
來源|Yahoo News / 撰文|簡秀枝
8/11/2021
1966年中國發生巨變中,學者岑家梧(1912-1966)被批鬥,在眾目睽睽下跳窗尋短,當時重摔落地,血流如注,但未斷氣,人群圍觀,指指點點,卻無人挺身救援或幫忙送醫。一個月後,有關部門送來小包裹,說是岑家梧遺物。家屬以為是骨灰,打開一看,只有岑家梧的一只眼鏡盒,𥚃頭放著生前配戴的近視眼鏡,以及一張皺巴巴的小紙條,上頭用廣東話寫著,「孩子,你要爭氣!」
藝術家岑龍(1957-)每每憶及這段陳年慘事,總是淚流滿面,悲不自勝。
留住香火 遠宿他鄉
1950年代,中國戰禍頻傳,衞生條件不好,流行病肆虐,岑家兩個襁褓閨女,都因傳染病夭折。岑龍2歲時候,就被帶到法國里昂遠親家寄養,希望留住香火。岑家梧夫婦實在太思念孩子,1965年左右,以為社會平靜了,把8歲的岑龍接回家,沒想到,翌年迎面而來的是中國鋪天蓋地的歷史浩劫。曾經負笈海外求學,大學任教的岑家梧,成為批鬥重點對象。岑家梧自認為對民族文化研究有功,頂天立地,不願隨批鬥起舞,更抗拒屈從耍猴戲碼,結果換來更大的人身攻擊,人格尊嚴被惡意踐踏侮辱,最後引恨跳窗,在墜落血泊中,慢慢死去。岑龍來不及享受飽學父親的啟蒙與教誨,母親也因是大學教授,批鬥之餘,下放勞改,家人四散,悽風苦雨,鋪陳出他的早熟人生。
孤獨遠行 宿命難違
岑龍常自嘲,他因為走得太遠而孤獨,也因為孤獨,而走得太遠,藝術,成為他大半生的慰藉與伴侶。因為兩位姐姐的夭折,岑龍打從呱呱落地開始,就背負著岑家香火傳承使命,2歲寄人籬下,遠親一家人,上班上課,各忙各的,小男孩學會用塗鴉來打發孤獨時間。逐漸,遠親看出他早慧的畫畫天賦,4歲就讓他到法國幼稚園美術班,學畫水彩,而他的成熟表現,總是迎來讚美。星期假日,擔任教職的遠親,經常帶他到美術館走動,參觀原作,所以,他比一般孩童幸運,很小就看過許多大師級作品,他有樣學樣,把天馬行空的想像,在空白紙張上塗抹,而他的陽光畫作,會成為大人的話題,也被被當作禮物,送給左鄰右舍,讓他很有成就感。大師的經典原作,美術館的靜肅氛圍,都成為他童年的直接養份,是眼力訓練的濫觴,也是讓他專注力培養的開始,他習慣安靜創作,也不害怕獨處。美術館的眾多名作中,他印象最深刻的是,爐火伴讀的小品之作,暟暟白雪中,山間小木屋,爐火燒得正旺,窮苦漁夫倚著火爐,縫補漁網,可愛的小女孩在木凳朗讀,漁夫沈浸在童言童語似的朗讀聲,爐火的嗶啵作響,成了天籟美聲,忘卻補魚的辛勞與隆冬的嚴寒。也許是因為離鄉背景,小男孩其實渴望那種有父母陪伴的天倫。這幅作品,烙印在她腦海,直到他長大,才知道繪畫的作者是芬蘭籍畫家阿克塞利・加倫-卡勒拉(Akseli Gallen-kallela,1865-1931),以芬蘭民族史詩《卡勒瓦拉》為主題的作品聞名,對芬蘭民族身份認同(identity)的形成,影響深遠。
父子同框 永遠神話
岑龍回到父母身邊後,有過短暫的父子同台競技。父親知道他喜歡畫畫,雖然不希望他往藝術發展,擔心他找不到飯碗,但內心深處,很以兒子繪畫天份自豪。有回父親帶著新買的紙筆給他,他心大喜隨手作畫,鉅細靡遺,畫得很用心,是他稚嫩童年中對洪山寶塔的印象,父親看了看,在另一張空白紙上,勾勒一座寶塔,要兒子補上山石林木,然後告訴他說,「畫畫,主要是畫感覺,要找到感覺去畫畫。三分象形,七分畫神。」父親最驕傲地題著「家梧父子春節試筆」。父子難得同台較勁,溫馨甜蜜,藝術真諦的傳遞,盡在不言中。岑龍經常感嘆父子緣淺,那一紙父子合作之作,早已在社會動盪的翻箱倒櫃中,不知去向,而父親無心插柳的闡述與教誨,讓他終身受益。20世紀3、40年代,中國大陸學術人才輩出,以中國人類學、民族學界的角度來說,就有「南岑北費」之說,「北費」,指的是費孝通;「南岑」,指的就是從海南走出的岑家梧。
飽學慈父 寧死不屈
岑家梧1912年出生於海南澄邁縣永發鎮排坡鄉岑後村,自幼父母雙亡,由兄長和姐姐撫養長大。這個出身貧寒的海南小伙子,苦學有成。從1927年到1932年,他從海南到廣州,從廣州到北平,然後又從北平回到廣州。無論境遇多麼困難,他一心執著求學。1927年,高小畢業的岑家梧,因沒錢付學費而輟學,離鄉到廣州打工,寄居在堂叔岑國英家中。次年,由岑國英資助,岑家梧進入讀廣東省第一中學。此後,與同鄉王興瑞從廣州到北平求學,途中獲得著名金石學家容庚教授的支持。1931年8月,岑家梧入讀北平私立輔仁高中,次年又因缺學費無奈退學。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求學,後來又轉居北平廣東會館,一方面,去學校旁聽,再者於北平圖書館自學。同時,為報刊撰文,用稿費勉強維持生活,常以燒餅度日。岑家梧在北平圖書館自學期間,到北京大學旁聽了著名民俗學家許地山教授的學術演講,引起了他對人類學的興趣。1932年,赴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就讀。在名師指導下,他勤奮研讀,打下了深厚的專業基礎。他對《古代社會》的作者摩爾根,長期深入印第安人部落作社會調查,深感敬佩,便立下志願,夢想著像摩爾根一樣,到偏鄉野地去研究中國的古代社會。
1934年,果然在堂兄岑廷樹資助下,岑家梧遠赴日本留學,在日本東京立教大學學習史前考古學。在日本3年,他寫成《史前藝術史》《史前史概論》和《圖騰藝術史》3部著作,先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。年僅20餘歲的岑家梧,連出3本專著,學術界罕見。3年後,岑家梧從日本學成歸國,繼續奮戰於中國人類學、民族學的第一線研究,對人類學、民族學、歷史學等學科,帶來奠基性或開拓性貢獻。在岑家梧54年的生命中,他在史前藝術史學、藝術學、民俗學、社會學、民族學等各個領域都有重大建樹,其著述數量之多、覆蓋領域之廣,同儕難以望其項背。這些著作,有的在他生前出版,有的則在他逝世多年之後,分批出版。包括《圖騰藝術史》、《史前藝術史》、《史前史概論》、《中國藝術論集》、《西南民族文化論叢》、《中國原始社會史稿》、《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》、《岑家梧學術論文選》、《洪水傳說集》、《劬燕集》。中國海南出版社出版了《瓊崖文庫》叢書,其中《岑家梧文集》收錄了岑家梧的主要著作。
頑強拼搏 藝術領航
出身這樣的書香世家,岑龍始終把父親的遭遇與不幸,裹藏在內心深處,而父親的「爭氣」叮嚀,終生烙印腦海。他承襲了父親兩項價值觀,一,不為厄運與噩境屈服。二,以知識翻轉命運。1960年代晚期,中國大陸的巨變,追使年輕人必須下鄉服務,因為很會畫畫,他曾虛報年齡,輾轉進入所謂的文工團,畫舞台佈景,擔任創作輔導,協助修改入選作品,同事之間,不乏優秀畫家,互動砌磋琢磨,吸收了不少養分。1979年,他離開工作單位,跳級報考西安美院美術研究所,他以《母親》的生動作品,取得合格入學機會,展開他的學歷文憑的重建工作。1980年獲得西安美術學院碩士學位,而後曾進入中國美術家協會,也曾是中國前衞當代藝術運動「八五思潮」的湖北省參與者,熱情青春,沒有留白。岑龍與同樣在湖北美術學院任教的同事,中國藝術家尚掦(1942-)熟識,有回在尚揚家,看到奧地利畫家埃貢・席勒(Egon Schiele,1890-1918)的,畫冊,岑龍對於席勒的病態美學,當下震撼,那帶有神經質的畫面與線條,讓人拍案叫好,展現出的色塊組合、人物結構、畫面氣氛,都令人有著驚懾衝突之感。岑龍從中領悟了繪畫主題結構的重要性,色彩佈局、景物鋪陳、人物虛實安排,筆觸運用等等,都必須服膺大局,才掌握氛圍,最後成就畫魂。
岑龍的創作風格,從表面上看來使用的是具象的技法和表現手段,但實質上,他追求的是抽象觀念的表達,尤其,他一直視繪畫為參悟生命,表達情感的方式。他接觸西方藝術很早,也比別人看了更多原創作品,其中幾個大師,他鍾愛有加,研究思考,也設法當作養分吸收,例如,哈爾斯(Frans Hals,1580-1666)、維拉斯奎茲(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Velazquez,1599-1660)、范戴克(Sir Anthony van Duck, 1599-1641)、林布蘭特(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,1606-1669)等古典大師,不管是邏輯內涵或外在技法,他都鞭僻入𥚃,窮追不捨。對於色彩的選擇與運用,筆觸力度和畫面結構的掌握,岑龍已經經過長年的實踐考驗,形成個人凝重厚實的繪畫特色,他以素樸的心靈和筆法,編織成自己的理想境界,然後用畫筆,傳遞愛和希望。岑龍常說,人生短暫,生命無常,軀體是有侷限性的,然而,昇華人性的輝光,透過藝術創作與分享,成為永恆不滅的精神資產,去暴戾之氣,還祥和氣息,讓社會靜好。
動畫開路 善緣相隨
人物造型,是岑龍最愛,他所描繪的人物造型,都是出自凝鍊構建,由人物造型,蛻變的插畫,則夾雜更多社會教義,與美學推廣。千禧年左右。岑龍曾去了一趟日本,日本是他喜歡久住地方。他待了3年多,在那裡除了行腳各風景名勝古蹟,參觀不少美術館博物館,吸收日本文化,也開始畫插畫。繪畫出道得早,技術的嫺熟洗煉達,自不在話下,加上縝密推敲過的東方情趣與創作視角,正好派上用場。他快筆勾勒,精緻挥灑,留下不少創作。素樸憨厚,拙趣盎然,是岑龍的插畫特色,深得日本出版公司的好評,後續許多插圖出版,如雪片般飛來,而絕無僅有的筆力與風格,得天獨厚。所謂岑龍古典中國風繪本《賣炭翁》,就是例子,當時洛陽紙貴,當他從日本,歸返中國時,國際出版商,亦步亦趨,一路追蹤岑龍回到大陸內地,去索取後續創作。因為應對國際出版,來自台灣,活躍海外的國際文化工作者林暄涵,因為精通日語英文,擔任過岑龍的翻譯工作,兩人結下日後合作推廣當代藝術作品的善緣。
然而,當林暄涵越了解岑龍作品內涵與際遇,越能肯定岑龍的創作內涵,也支持他要為亡父「爭氣」,因此接手岑龍的藝術代理工作,一肩挑起岑龍的國際展銷、學術論述等重責大任。林暄涵一不作,二不休,開始思考當代藝術至關重要的空間問題。2009年起,在台南文化古都成立「涵藝術空間」,接著,也在物價昂貴、寸土寸金的美國紐約,也成立畫廊據點。12年的孜矻耕耘,林暄涵已經把岑龍的創作,透過藝術展覽、論文集出版,也參與國際藝術博覽會,與在地重要貴賓活動,經常聯手合辦,讓岑龍的作品,都在地父老,建立友善關係。岑龍也千里迢迢,來台參與盛會,會會粉絲與收藏群。尤其可喜的是,林暄涵動用國際策展人關係,與跨城人脈支援,把岑龍推上威尼斯藝術雙年展,讓岑龍的藝術話題,與國際威尼斯盛會,同框共彩。
2019年《蒼穹星光—岑龍和他的藝術》在義大利威尼斯馬爾他聖若望教堂,就是參加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的成功案例,受到關注。岑龍在取名為「光的追隨者」出版品上,明白地提出自我定位。他說,我就是一個畫畫的畫家(A Painter),岑龍強調,投入藝術創作,完全是他一生一世的志業,而創作的題材,包括描述他的生活場景,之外,就是用他的自我的經歷,與情感記憶作畫。面對大時代的動盪與悲劇,國恨家仇,那裡計較得完,他一聲長嘆。憨厚慈祥的父母,總是三申五令,教導著他,用善良去戰勝憎恨,讓他點滴在心頭。岑龍原來在湖北美術學院油畫系,任教多年之後,興起專職藝術家的念頭,於是2004年,他毅然辭去教職,全力投入藝術創作。綜觀岑龍超過一甲子的塗抹與創作,風格有變,也有不變。比如說,他早年喜歡具象寫實,求型體神似,作為自我挑戰目標,隨著年歲的增長,岑龍現在回到減法人生,力求簡約。他去地域性,去形體化,希望在藝術本真,深刻挖掘,尤其聚焦在人性的探索上。
愛光希望、尊嚴和價值
於是,他畫愛,畫光,畫希望,畫人性尊嚴,更畫生命價值。以下是他創作的幾種代表作:
一、夢想起飛
這是他長年惦記亡父的苦難,緬懷永逝的天倫碎夢的心境之作。岑龍藉著伊卡洛斯(Icarus)的希臘神話故事,使用蠟造的翼逃離克里特島時,因飛得太高,雙翼遭太陽溶化,跌落水中喪生。岑龍以渴望自由的社會菁英,使用簡陋飛傘,異想天開地希望飛出藩籬與框架,追逐他的夢想願景,不問自明,那是粉身碎骨的飛躍。
二、生命禮讚
懷有身孕的母親,敞開斗篷,接受小男孩手上的野花束,孺慕之情,自然天成,一旁溫馴綿羊,昂首分享這份親情。岑龍利用光線描繪技法,把地面反射的柔光,營造出聖潔氛圍,彷彿是聖母下凡,慈暉滿溢。疏簡繁複合宜搭配,有考究筆觸和線條,他以硬毛筆刷和油畫刀製造紋理,隆起的肚腩,堅實粗燥的裸腳,也彷彿是實實在在的大地之母,真摰動人。
三、起風日子
以力大無窮的人體構成,配合周遭抽象背景,風暴來臨之前,兩名水手,急拉風帆。屈身下壓的光頭男,鏗鏘有力,是顆不屈不撓的堅硬頭顱,不管是濕滑船板上,兩雙巨腳掌,貼合地面,密實安定,抑或4隻武孔紮實手臂,抓緊繩索,是力量、愛、希望與信念的集大成,煞那定格的瞬間,有如儀式性十足的紀念碑,人定勝天、風雨生信心。
四、田原牧歌
一抹湛藍,扣住西下夕陽,村婦一手抱幼娃,一手灑麥種,略帶疲憊老農與耕牛,靜默地踏上歸途,任勞任怨,泰然自若,臨風搖曳的雜草,刻畫出深沈認命的田原牧歌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,串聯著祥和安寧,日復一日,期待那入土的種子,落地長根,生生不息的宇宙運行,引領著人世間的周而復始,代代傳承。
五、你捶我打
中國禪宗師徒間道法傳授,常常舉行授與衣缽的儀式。比喻技術、學術的師徒相傳。泛指師生間,一切思想、學術及技能,衣缽相傳,薪火不絕。在家庭何嘗不是如此,老鐵匠燒紅熾熱鐵塊,你一錘我一打,凝結著辛苦汗滴,交織出堅強信念,天下沒有不勞而獲,鐵杵磨成繡花針的工匠精神與智慧,需要代代相傳。
六、登高放遠
面對迢遙千里路,小女孩沒有絲毫膽卻懦弱,只是臨行密密縫,意恐遲遲歸的慈母叮嚀,嚴父告誡,孩子,別怕,爸爸在遙遠的他鄉,守護著你。9歲喪父的岑龍,大半生背負著漂泊與孤獨,他習慣這樣的獨處,也慢慢孤獨成僻。人前人後,登高放遠,隨遇而安,樂觀進取。只是漫漫天涯路,餐風露宿過後,始終找不到天倫歸巢。那是他終其一生的迷惘,更是刻骨銘心的殤與痛。